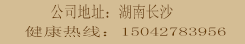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旅游 > 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毛二更
当前位置: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旅游 > 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毛二更

![]() 当前位置: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旅游 > 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毛二更
当前位置: 沙特阿拉伯 > 沙特阿拉伯旅游 > 梦里花落知多少三毛二更
阅读进度:30%
Feb
28
这个阅读速度是每分钟.95个字的速度。正常阅读速度是每分钟-个字。你用了多久?
正文字数:
阅读时间:20分钟
梦里梦外
我不很明白,为什么特别是现在,在窗帘已经垂下,而门已紧紧闩好的深夜,会想再去记述一个已经逝去的梦。
也问过自己,此刻海潮回响,树枝拍窗,大风凄厉刮过天空,远处野狗嗥月,屋内钟声滴答。这些,又一些夜的声音应该是睡眠中的事情,而我,为什么却这样的清醒着在聆听,在等待着一些白日不会来的什么。
便是在这微寒的夜,我又披着那件老披肩,怔怔地坐在摇椅上,对着一盏孤灯出神。
便是又想起那个梦来了,而我醒着,醒在漆黑的夜里。
这不是惟一纠缠了我好多年的梦,可是我想写下来的,在今夜却只有这一个呢。
我仿佛又突然置身在那座空旷的大厦里,我一在那儿,惊惶的感觉便无可名状地淹了上来,没有什么东西害我,可是那无边无际的惧怕,却是渗透到皮肤里,几乎彻骨。
我并不是一个人,四周围着我的是一群影子似的亲人,知道他们爱我,我却仍是说不出的不安,我感觉到他们,可是看不清是谁,其中没有荷西,因为没有他在的感觉。
好似不能与四周的人交谈,我们没有语言,我们只是彼此紧靠着,等着那最后的一刻。
我知道,是要送我走,我们在无名的恐惧里等着别离。
我抬头看,看见半空中悬空挂着一个扩音器,我看见它,便有另一个思想像密码似的传达过来--你要上路了。
我懂了,可是没有听见声音,一切都是完全安静的,这份死寂更使我惊醒。
没有人推我,我却被一股巨大的力量迫着向前走。
--前面是空的。
我怕极了,不能叫喊,步子停不下来,可是踩每一步都是空的!
我拼命向四周张望着,寻找绕着我的亲人。发觉他们却是如影子似的向后退,飘着在远离,慢慢地飘着。
那时我更张惶失措了,我一直在问着那巨大无比的"空"--我的箱子呢,我的机票呢,我的钱呢?要去什么地方,要去什么地方嘛!
亲人已经远了,他们的脸是平平的一片,没有五官,一片片白的脸。
有声音悄悄地对我说,不是声音,又是一阵密码似的思想传过来--走的只有你。
还是管不住自己的步伐,觉着冷,空气稀薄起来了,
的浓雾也来了,我喊不出来,可是我是在无声地喊--不要!不要!
然后雾消失不见了,我突然面对着一个银灰色的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个弧形的洞,总是弧形的。
我被吸了进去。
接着,我发觉自己孤零零地在一个火车站的门口,一眨眼,我已进去了,站在月台上,那儿挂着明显的阿拉伯字--六号。
那是一个欧洲式的老车站,完全陌生的。
四周有铁轨,隔着我的月台,又有月台,火车在进站,有人上车下车。
在我的身边,是三个穿着草绿色制服的兵,肩上缀着长长的小红牌子。其中有一个在抽烟,我一看他们,他们便停止了交谈,专注地望着我,彼此静静地对峙着。
又是觉着冷,没有行李,不知要去哪里,也不知置身何处。
视线里是个热闹的车站,可是总也听不见声音。
又是那股抑郁的力量压了上来,要我上车去,我非常怕,顺从地踏上了停着的列车,一点也不敢挣扎。
--时候到了,要送人走。
我又惊骇地从高处看见自己,挂在火车踏板的把手上,穿着一件白衣服,蓝长裤,头发乱飞着,好像在找什么人。我甚而与另一个自己对望着,看进了自己的眼睛里去。
接着我又跌回到躯体里,那时,火车也慢慢地开动了。
我看见一个红衣女子向我跑过来,她一直向我挥手,我看到了她,便突然叫了起来--救命!救命!
已是喊得声嘶力竭了,她却像是听不见似的,只是笑吟吟地站住了,一任火车将我载走。
"天啊!"我急得要哭了出来,仍是期望这个没有见过的女子能救我。
这时,她却清清楚楚地对我讲了一句中文。
她听不见我,我却清晰地听见了她,讲的是中文。整个情景中,只听见过她清脆的声音,明明是中文的,而我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用中文的啊!
风吹得紧了,我飘浮起来,我紧紧地抱住车厢外的扶手,从玻璃窗里望去,那三个兵指着我在笑。
他们脸上笑得那么厉害,可是又听不见声音。
接着我被快速地带进了一个幽暗的隧道,我还挂在车厢外飘着,我便醒了过来。
是的,我记得第一次这个噩梦来的时候,我尚在丹娜丽芙岛,醒来我躺在黑暗中,在彻骨的空虚及恐惧里汗出如雨。
以后这个梦便常常回来,它常来叫我去看那个弧形的银灰色的洞,常来逼我上火车,走的时候,总是同样的红衣女子在含笑挥手。
梦,不停地来纠缠着我,好似怕我忘了它一般的不放心。
去年,我在拉芭玛岛,这个梦来得更紧急,交杂着其他更凶恶的信息。
夜复一夜,我跌落在同样的梦里不得脱身。在同时,又有其他的碎片的梦挤了进来。
有一次,梦告诉我:要送我两副棺材。
我知道,要有大祸临头了。
然后,一个阳光普照的秋日,荷西突然一去不返。
我们死了,不是在梦中。
我的朋友,在夜这么黑,风如此紧的深夜,我为什么对你说起上面的事情来呢?
我但愿你永远也不知道,一颗心被剧烈的悲苦所蹂躏时是什么样的情形,也但愿天下人永远不要懂得,血雨似的泪水又是什么样的滋味。
我为什么又提起这些事情了呢,还是让我换一个题材,告诉你我的旅行吧。
是的,我结果是回到了我的故乡去,梦走了,我回台湾。
春天,我去了东南亚、香港,又绕回到台湾。
然后,有一天,时间到了,我在桃园机场,再度离开家人,开始另一段长长的旅程。
快要登机的时候,父亲不放心地又叮咛了我一句:确定自己带的现款没有超过规定吗?
你的钱太杂了,又是马克,又是西币,又是美金和港纸。
我坐在亲人围绕的椅子上开始再数一遍我的钱,然后将它们卷成一卷,胡乱塞在裙子口袋里去。
就在那个时候,似曾相识的感觉突然如同潮水似的渗了上来,悄悄地带我回到了那个梦魇里去。有什么东西,细细凉凉地爬上了我的皮肤。
我开始怕了起来,不敢多看父母一眼,我很快地进了出境室,甚而没有回头。我怕看见亲人面貌模糊,因为我已被梦捉了过去,是真真实实地踏进梦里去了。梦里他们的脸没有五官。
我进去了,在里面的候机室里喝着柠檬茶,我又清醒了,什么也不再感觉。
然后长长的通道来了,然后别人都放了手。只有我一个人在大步地走着,只有我一个人,因为别人是不走了--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我的朋友,不要觉得奇怪,那只是一霎的感觉,一霎间梦与现实的联想而引起的回忆而已,哪有什么梦境成真的事情呢?
过了几天,我在香港上机,飞过昆明的上空,飞过千山万水,迎着朝阳,瑞士在等着我,正如我去时一样。
日内瓦是法语区,洛桑也是。
以往我总是走苏黎世那一站,同样的国家,因为它是德语区,在心理上便很不同了。
常常一个人旅行,这次却是不同,有人接,有人送,一直被照顾得周全。
我的女友熟练地开着车子,从机场载着我向洛桑的城内开去。
当洛桑的火车站在黎明微寒的阳光下,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是迷惑得几乎连惊骇也不会了--这个地方我来过的,那个梦中的车站啊!
我怎么了,是不是死了?不然为什么这个车站跑了出来,我必是死了的吧!
我悄悄地环视着车中的人,女友谈笑风生,对着街景指指点点。
我又回头去看车站,它没有消失,仍是在那儿站着。
那么我不是做梦了,我摸摸椅垫,冷冷滑滑的,开着车窗,空气中有宁静的花香飘进来。这不是在梦中。
我几乎忍不住想问问女友,是不是,是不是洛桑车站的六号月台由大门进去,下楼梯,左转经过通道,再左转上楼梯,便是那儿?是不是入口处正面有一个小小的书报摊?是不是月台上挂着阿拉伯字?是不是卖票的窗口在右边,询问台在左边?还有一个换钱币的地方也在那儿,是不是?
我结果什么也没有说,到了洛桑郊外的女友家里,我很快地去躺了下来。
这样的故事,在长途旅行后跟人讲出来,别人一定当我是太累了,快累病了的人才会有的想像吧。
几天后,我去了意大利。
当我从翡冷翠又回到瑞士洛桑的女友家时,仍是难忘那个车站的事情。
当女友告诉我,我们要去车站接几个朋友时,我迟疑了一下,仍是很矛盾地跟去了。
我要印证一些事情,在我印证之前,其实已很了然了。因为那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个车站,虽然今生第一次醒着进去,可是梦中所见,都得到了解释,是它,不会再有二个可能了,我真的去了,看了,也完全确定了这件事。
我的朋友,为什么我说着说着又回到梦里去了呢?你知道我下一站是维也纳,我坐飞机去奥国,行程里没有坐火车的安排,那么你为什么害怕了呢?你是怕我真的坐上那节火车吧!没有,我的计划里没有火车呢。
在瑞士法语区,除了我的女友一家之外,我没有相识的人,可是在德语区,却有好几家朋友已有多年的交往了。
对于别的人,我并不想念,住在阿庭根的拉赫一家却是如同我的亲人似的。既然已在瑞士了,总忍不住想与她通一次电话。
电话接通了。歌妮,拉赫十九岁的女儿听说是我,便尖叫了起来:"快来,妈妈,是Echo,真的,在洛桑。"
拉赫抢过话筒来,不知又对谁在唤:
"是Echo,回来了,你去听分机。"
"一定要来住,不让你走的,我去接你。"拉赫在电话中急促地说。
"下一站是去维也纳哥哥处呢!不来了,电话里讲讲就好!"我慢慢地说。
"不行!不看见你不放心,要来。"她坚持着。
我在这边沉默不语。
"你说,什么时候来,这星期六好吗?"
"真的只想讲讲电话,不见面比较好。"
"达尼埃也在这儿,叫他跟你讲。"
我并不知道达尼埃也在拉赫家,他是我们加那利群岛上邻居的孩子,回瑞士来念书已有两年了。他现在是歌妮的男朋友。
"喂!小姐姐口也--"
一句慢吞吞的西班牙文传过来,我的胃马上闪电似的绞痛起来了。
"达尼埃--"我几乎哽咽不能言语。
"来嘛!"他轻轻地说。
"好!"
"不要哭,Echo,我们去接你,答应了?"
"答应了。"
"德莱沙现在在洛桑,要不要她的电话,你们见见面。"又问我。
"不要,不想见太多人。"
"大家都想你,你来,乌苏拉和米克尔我去通知,还有希伯尔,都来这儿等你。"
"不要!真的,达尼埃,体恤我一点,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拜托你!"
"星期六来好不好?再来电话,听清楚了,我们来接。"
"好!再见!"
"喂!"
"什么?"
"安德列阿说,先在电话里拥抱你,欢迎你回来。"
"好,我也一样,跟他说,还有奥托。"
"不能赖哦!一定来的哦!"
"好,再见!"
挂断了电话,告诉女友一家,我要去阿庭根住几日。
"你堂哥不是在维也纳等吗?要不要打电话通知改期?"女友细心地问。
"哥哥根本不知道我要去,在台北时太忙太乱了,没有写信呢!"
想想也是很荒唐,也只有我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准备自己到了维也纳才拉了箱子去哥哥家按铃呢!十三年未见面,去了也不早安排。
"怎么去阿庭根?"女友问。
"他们开车来接。"
"一来一回要六小时呢,天气又不太好。"
"他们自己要来嘛!"我说。
女友沉吟了一下:
"坐火车去好口罗!到巴塞尔,他们去那边接只要十五分钟。"
"火车吗?"我慢吞吞地答了一句。
"每个钟头都有的,好方便,省得麻烦人家开车。"女友又利落地说。
"他们要开车来呢!说--好几年没来洛桑了,也算一趟远足。"
"--我不要火车。"
"火车又快又舒服,去坐嘛!"又是愉快地在劝我。
"也好!"迟迟疑疑地才答了一句。
要别人远路开车来接,亦是不通人情的,拉赫那边是体恤我,我也当体恤她才是。再说,那几天总又下着毛毛雨。
"这么样好了,我星期六坐火车去,上了车你便打电话过去那边,叫他们去巴塞尔等我,跟歌妮讲,她懂法文。"我说。
--可是我实在不要去上火车,我怕那个梦的重演。
要离开洛桑那日的早晨,我先起床,捧着一杯热茶,把脸对着杯口,让热气雾腾腾地漫在脸上。
女友下楼来,又像对我说,又似自言自语:"你!今天就穿这身红的。"
我突然想起我的梦来,怔怔地望着她出神。
午间四点那班车实在有些匆促,女友替我寄箱子,对我喊着:"快!你先去,六号月台。"
我知道是那里,我知道怎么去,这不过是另外一次上车,重复过太多次的事情了。
我冲上车,丢下小手提袋,又跑到火车踏板边去,这时我的女友也朝我飞奔而来了。
"你的行李票!"她一面跑一面递上票来。这时,火车已缓缓地开动了。
我挂在车厢外,定定地望着那袭灰色车站中鲜明的红衣--梦中的人,原来是她。
风来了,速度来了,梦也来了。
女友跟着车子跑了几步,然后站定了,在那儿挥手又挥手。
这时,她突然笑吟吟地喊了一句话:"再见了!要乖乖的呀!"
我就是在等她这句话,一旦她说了出来,仍是惊悸。
心里一阵哀愁漫了出来,喉间什么东西升上来卡住了。
难道人间一切悲欢离合,生死兴衰,在冥冥中早已有了定数吗?
这是我的旅程中的最后一次听中文,以后大概不会再说什么中文了。
我的朋友,你看见我一步一步走入自己的梦中去,你能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吗?这不过又是一次心灵与心灵的投契和感应,才令我的女友说出梦中对我的叮咛来。事实上这只是巧合罢了,与那个去年大西洋小岛上的梦又有什么真的关联呢?
车厢内很安静,我选的位子靠在右边单人座,过道左边坐着一对夫妇模样的中年人,后面几排有一个穿风衣的男人闭着眼睛在养神。便再没有什么人了。
查票员来了,我顺口问他:"请问去巴塞尔要多久?"
"两小时三十三分。"他用法语回答我。
"我不说法语呢!"我说的却是一句法语。
"两小时三十三分。"他仍然固执地再重复了一遍法语。
我拿出惟一带着的一本中文书来看。火车飞驰,什么都被抛在身后了。
山河岁月,绵绵地来,匆匆地去。什么人?什么人在赶路?不会是我。我的路,在去年的梦里,已被指定是这一条了,我只是顺着路在带着我远去罢了。
列车停了一站又一站,左边那对夫妇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
有人上车,有人下车,好似只有我,是驶向终站惟一的乘客。
身后有几个人走过来,大声地说笑着,他们经过我的身边,突然不笑了,只是盯住我看。
梦幻中的三个兵,正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草绿色的制服,肩上缀着小红牌子。
看我眼熟吗?其实我们早已见过面了。
我对他们微微地笑了一笑,不怀好意地笑着。心里却浮上了一种奇异虚空的感觉来。
窗外流过一片陌生的风景,这里是蜂蜜、牛奶、巧克力糖、花朵还有湖水的故乡。大地挣扎的景象在这儿是看不见的,我反倒觉得陌生起来。
难道在我的一生里,熟悉过怎么样的风景吗?没有,其实什么也没有熟悉过,因为在这劳劳尘梦里,一向行色匆匆。
我怔怔地望着窗外,一任铁轨将我带到天边。
洛桑是一个重要的起站,从那儿开始,我已是完完全全地一个人了,茫茫天涯路,便是永远一个人了。
我是那么的疲倦,但愿永远睡下去不再醒来。
车厢内是空寂无人了,我贴在玻璃窗上看雨丝,眼睛睁得大大的,不能休息。
好似有什么人又在向我传达着梦中的密码,有思想叹息似的传进我的心里,有什么人在对我悄悄耳语,那么细微,那么缓慢地在对我说--苦海无边……
我听得那么真切,再要听,已没有声息了。
"知道了!"
我也在心里轻轻地回答着,那么小心翼翼地私语着,在交换着一个不是属于这个尘世的秘密。
懂了,真的懂了。
这一明白过来,结在心中的冰天雪地顿时化作漫天杏花烟雨,寂寂、静静、茫茫地落了下来。
然而,春寒依旧料峭啊!
我的泪,什么时候竟悄悄地流了满脸。
懂了,也醒了。
醒来,我正坐在梦中的火车上,那节早已踏上了的火车。
不飞的天使
往巴塞尔的旅程好似永远没有尽头。火车每停一个小站,我都从恍惚的睡梦中惊醒,站上挂着的总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藏身在这飞驰的巨兽里使我觉得舒适而安全,但愿我的旅程在这单调的节奏里永远晃过去直到老死。
对于去拉赫家做客的事情实在是很后悔的,这使我非常不快乐。要是他们家是一座有着树林围绕的古堡,每天晚餐时彼此才见一次面,那么我的情况将会舒坦得多了。
与人相处无论怎么感情好,如果不是家人的亲属关系,总是使我有些紧张而不自在。
窗外一片蒙,雨丝横横地流散着。我呵着白气,在玻璃上画着各样的图画玩。
车子又停在一个小镇,我几乎想站起来,从那儿下车,淋着寒冷的雨走出那个地方,然后什么也不计划,直走到自己消失。
火车一站又一站地穿过原野,春天的绿,在细雨中竟也显得如此寂寞。其实还不太晚,还有希望在下一次停车的时候走出去,还来得及丢掉自己,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做一个永远逃亡的士兵。
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做,更别说下车了,这只是一霎间的想法罢了。
我又闭上眼睛,第一次因为心境的凄苦觉得孤单。
当火车驶入巴塞尔车站时,一阵袭上来的抑郁和沮丧几乎使我不能举步,那边月台上三个正在张望的身影却开始狂喊着我的名字,没命地挥着手向我这节车厢奔来。
对的,那是我的朋友们在唤我,那是我的名字,我在人世的记号。他们叫魂似的拉我回来又是为了什么?
我叹一口气,拿起自己的小提包,便也含笑往他们迎上去。
"哎呀,Echo!"歌妮抢先扑了上来。
我微笑地接过她,倦倦地笑。
在歌妮身后,她的男朋友,我们在加那利群岛邻居的孩子达尼埃也撑着拐杖一步一跳地赶了上来。
我揉揉达尼埃的那一头乱发慢慢地说:"又长高了,都比我高一个头了。"
说完我踮起脚来在他面颊上亲了一下。
这个男孩定定地看着我,突然眼眶一红,把拐杖往歌妮身上一推,双手紧紧环住我,什么也不说,竟是大滴大滴地流下泪来。
"不要哭!"我抱住达尼埃,也亲了他一下。
"歌妮!你来扶他。"我将达尼埃交给在一边用手帕蒙住眼睛的小姑娘。
这时我自己也有些泪湿,匆匆走向歌妮的哥哥安德列阿,他举过一只手来绕住我的肩,低头亲吻我。
"累不累?"轻轻地问。
"累!"我也不看他,只是拿手擦眼睛。
"你怎么也白白的了?"我敲敲他的左手石膏。
"断了!最后一次滑雪弄的,肋骨也缠上了呢!"
"你们约好的呀!达尼埃伤腿你就断手?"
我们四个人都紧张,都想掩饰埋藏在心底深处的惊骇和疼痛,而时间才过去不久,我们没法装作习惯。在我们中间,那个亲爱的人已经死了。
"走吧!"我打破了沉默笑着喊起来。
我的步子一向跨得大,达尼埃跟歌妮落在后面了,只安德列阿提着我的小行李袋跟在我旁边。
下楼梯时,达尼埃发狠猛跳了几步,拿起拐杖来敲我的头:"走慢点,喂!"
"死小孩!"我回过头去改用西班牙文骂起他来。
这句话脱口而出,往日情怀好似出闸的河水般淹没了我们,气氛马上不再僵硬了。达尼埃又用手杖去打安德列阿的痛手,大家开始神经质地乱笑,推来挤去,一时里不知为什么那么开心,于是我们发了狂,在人群里没命地追逐奔跑起来。
我一直冲到安德列阿的小乌龟车旁才住了脚,趴在车盖上喘气。
"咦!你们怎么来的?"我压着胸口仍是笑个不停。
歌妮不开车,达尼埃还差一年拿执照,安德列阿只有一只手。
"你别管,上车好口罗!"
"喂!让我来开!让我来开嘛!"我披头散发地吵,推开安德列阿,硬要挤进驾驶座去。
"你又不识路。"
"识的!识的!我要开嘛!"
安德列阿将我用力往后座一推,我再要跟他去抢他已经坐在前面了。
"去莱茵河,不要先回家,拜托啦!"我说。
安德列阿从后视镜里看我一眼,当真把方向盘用力一扭,单手开车的。
"不行!妈妈在等呀!"歌妮叫了起来。
"去嘛!去嘛!我要看莱茵河!"
"又不是没看过,等几天再去好口罗!"达尼埃说。
"可是我没有什么等几天了,我会死掉的!"我又喊着。
"别发疯啦!胡说八道的。"达尼埃在前座说。
我拿袖子捂住眼睛,仰在车垫上假装睡觉,一手将梳子递给歌妮:"替我梳头,拜托!"
我觉着歌妮打散了我已经毛开了的粗辫子,细细地在刷我的头发。
有一年,达尼埃的母亲在加那利群岛死了,我们都在他家里帮忙照顾他坐轮椅的父亲。
拉赫全家过几日也去了群岛,我也是躺在沙发上,歌妮在一旁一遍又一遍地替我梳头,一面压低了声音讲话,那时候她才几岁?十六岁?
"有一件事情--"我呻吟了一声。
"什么?"
"我们忘了去提我的大箱子了!"说完我格格地笑起来。
"怎么不早讲嘛!"安德列阿喊了起来。
"管它呢!"我说。
"你先穿我的衣服好口罗!明天再去领。"歌妮说。
"丢掉好啦!"我愉快地说。
"丢掉?丢掉?"达尼埃不以为然地叫起来。
"什么了不起,什么东西跟你一辈子哦!"说完我又笑了起来。
阿庭根到了,车子穿过如画的小镇。一座座爬满了鲜花的房子极有风味地扑进眼里。欧洲虽然有些沉闷,可是不能否认它仍有感人的古老的光辉。
我们穿过小镇又往郊外开去。夕阳晚风里,一幢瑞士小木屋美梦似的透着黄黄的灯光迎接我们回家。楼下厨房的窗口,一幅红白小方格的窗帘正在飘上飘下。
这哪里只是一幢普通人家的房子呢!这是天使住的地方吧!它散发着的宁静和温馨使我如此似曾相识,我自己的家,也是这样的气氛呢!
我慢慢地下了车,站在那棵老苹果树下,又是迟疑,不愿举步。
拉赫,我亲爱的朋友,正扶着外楼梯轻快地赶了过来。
"拉赫!"我拨开重重的暮色向她跑去。
"哦!Echo!我真快乐!"拉赫紧紧地抱住我,她的身上有淡淡的花香。
"拉赫!我很累!我全身什么地方都累。"
说着我突然哭了起来。
这一路旅行从来没有在人面前流泪的,为什么在拉赫的手臂里突然真情流露,为什么在她的凝视下使我泪如泉涌?
"好了!好了!回来就好!看见你就放心了,谢谢上天!"
"行李忘在车站了!"我用袖子擦脸,拉赫连忙把自己抹泪的手帕递给我。
"行李忘了有什么要紧!来!进来!来把过去几个月在中国的生活细细地讲给我听!"
我永远也不能抗拒拉赫那副慈爱又善良的神气,她看着我的表情是那么了解又那么悲恸,她清洁朴实的衣着,柔和的语气,都是安定我的力量,在她的脸上,一种天使般的光辉静静地光照着我。
"我原是不要来的!"我说。
"不是来,你是回家了!如果去年不是你去了中国,我们也是赶着要去接你回来同住的。"
拉赫拉着我进屋,拍松了沙发的大靠垫,要我躺下,又给我开了一盏落地灯,然后她去厨房弄茶了。
我置身在这么温馨的家庭气氛里,四周散落有致地堆着一大叠舒适的暗花椅垫,古老的木家具散发着清洁而又殷实的气息,雪亮的玻璃窗垂挂着白色荷叶边的纱帘,绿色的盆景错落地吊着,餐桌早已放好了,低低的灯光下,一盘素雅的野花夹着未点的蜡烛等我们上桌。
靠近我的书架上放着几个相框,其中有一张是荷西与我合影,衬着荻伊笛火山的落日,两个人站在那么高的岩石上好似要乘风飞去。
我伸手去摸摸那张两年前的照片,发觉安德列阿正在转角的橡木楼梯边托着下巴望着我。
"小姐姐,我的客房给你睡。"达尼埃早先是住在西班牙的瑞士孩子,跟我讲话便是德文和西文夹着来的。
"你在这里住多久?"我喊过去。
"住到腿好!你呢?"他又叫过来,是在楼梯边的客房里。
"我马上就走的呢。"
"不可以马上走的,刚刚来怎么就计划走呢!"
拉赫搬着托盘进来说,她叹了口气,在我对面坐下来沏茶,有些怔怔地凝望着我。
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这家人孩子的朋友还是父母的朋友,我的情感对两代人都那么真诚而自然,虽然表面上看去我们很不相同,其实在内心的某些特质上我们实是十分相近的。
虽是春寒料峭,可是通阳台的落地窗在夜里却是敞开的,冷得很舒服。歌妮在二楼的木阳台上放音乐。
"爸爸回来了!"歌妮喊起来。
本是脱了靴子躺在沙发上的,听说奥托回来了,便穿着毛袜子往门外走去。
夜色浓了,只听见我一个人的声音在树与树之间穿梭着:"奥帝,我来了!是我呀!"
我从不唤他奥托,我是顺着拉赫的唤法叫他奥帝的。
奥帝匆匆忙忙穿过庭园,黑暗中步子是那么稳又那么重,他的西装拿在手里,领带已经解松了。
我开了门灯,跑下石阶,投入那个已过中年而依旧风采迷人的奥帝手臂里去,他棕色的胡子给人这样安全的欢愉。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奥帝只重复这一句话,好似我一向是住在他家里的一样。
拉赫是贤慧而从容的好主妇,美丽的餐桌在她魔术般的手法下,这么丰丰富富地变出来。外面又开始下着小雨,夜却是如此的温暖亲切。
"唉!"奥帝满足地叹了口气,擦擦两手,在灯下微笑。
"好!Echo来了,达尼埃也在,我们总算齐了。"他举起酒杯来与我轻轻碰杯。
拉赫有些心不在焉,忡忡地只是望着我出神。
"来!替你切肉。"我拿过与我并肩坐着的安德列阿的盘子来。
"你就服侍他一个人。"达尼埃在对面说。
"他没有手拿刀子,你有拐杖走路呢!"
达尼埃仍是羡慕地摇摇他那一头鬈毛狗似的乱发。
我们开始吃冰淇淋的时候,安德列阿推开椅子站了起来。
"我去城里跳舞。"他说。
我们停住等他走,他竟也不走,站在那儿等什么似的。灯光下看他,实在是一个健康俊美的好孩子。
"你怎么不走?"歌妮问他,又笑了起来。
"有谁要一起去?"他有些窘迫地说,在他这个年纪这样开口请人已很难得了。
"我们不去,要说话呢!"我笑着说。
"那我一个人去啦!"他粗声粗气地说,又看了我一眼,重重地拉上门走了。
我压低声音问拉赫:"安德列阿几岁了?"
"大口罗!今年开始做事了。"
"不搬出去?像一般年轻人的风气?"
"不肯走呢!"拉赫笑着说。
如果我是这家的孩子,除非去外国,大概也是舍不得离开的吧!
"以前看他们都是小孩子,你看现在歌妮和达尼埃--"我笑着对拉赫说,那两个孩子你一口我一口地在分冰淇淋呢!
"再过五年我跟歌妮结婚。"达尼埃大声说。
"你快快出来赚钱才好,歌妮已经比你快了!"我说。
"孩子们长得快!"拉赫有些感喟,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一对孩子。
"怎么样?生个火吧?"奥帝问我们。
其实这个家里是装了暖气的,可是大家仍是要个壁炉,我住在四季如春的加那利群岛,对这种设备最是欢喜。
对着炉火,我躺在地上,拉赫坐在摇椅里织着毛线,奥帝伸手来拍拍我,我知道他要讲大道理了,一下子不自在起来。
"Echo,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好再痛苦下去。"
被他这么碰到了痛处,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拿起垫子来压住脸。
"加那利群岛不该再住了,倒是想问问你,想不想来瑞士?"
"不想。"
"你还年轻,那个海边触景伤情,一辈子不可以就此埋下去,要有勇气追求新的生活--"
"明天就走,去维也纳。"我轻轻地说。
"箱子还在车站,明天走得了吗?"
"火车站领出来就去飞机场。"
"票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不要急,今天先睡觉,休息几天再计划好了。"拉赫说。
"希伯尔还要来看你呢!"达尼埃赶快说。
"谁叫你告诉他的?"我叹了口气。
"我么?乌苏拉、米克尔、凯蒂和阿尔玛他们全都没说呢!"达尼埃冤枉地叫了起来。
"谁也不想见,我死了!"我拿垫子又蒙住脸。
"Echo,要是你知道,去年这儿多少朋友为你痛哭,你就不会躲着不肯见他们了。"拉赫说着便又拿手帕擦眼角。
"拉赫,我这里死了,这里,你看不见吗?"我敲敲胸口又叹了口气,眼泪不干地流个不停。
"要不要喝杯酒?嗯!陪奥帝喝一杯白兰地。"奥帝慈爱地对我举举杯子。
"不了!我去洗碗!"我站起来往厨房走去。
这是一个愉快又清洁的卧房,达尼埃去客厅架了另外一个小床,别人都上楼去了。
我穿着睡袍,趴在卧室的大窗口,月光静静地照着后院的小树林,枝丫细细地映着朦朦的月亮,远天几颗寒星,夜是那么的寂静,一股幽香不知什么风将它吹了进来。
我躺在雪白的床单和软软的鸭绒被里,仿佛在一个照着月光的愁人的海上飘进了梦的世界。
"小姐姐!"有人推开房门轻轻地喊我。
"谁?"
"达尼埃!已经早晨九点了。"
我不理他,翻过身去再睡。
"起来嘛!我们带你去法国。"
我用枕头蒙住了头,仍是不肯动。如果可以一直如此沉睡下去又有多好,带我回到昨夜的梦里不要再回来吧!
我闭着眼睛,好似又听见有人在轻唤我,在全世界都已酣睡的夜里,有人温柔地对我低语:"不要哭,我的,我的--撒哈拉之心。"
世上只有过这么一个亲人,曾经这样捧住我的脸,看进我的眼睛,叹息似的一遍又一遍这样轻唤过我,那是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私语,那是我在世上惟一的名字--撒哈拉之心。
那么是他来过了?是他来了?夜半无人的时候,他来看我?在梦与梦的夹缝里,我们仍然相依为命,我们依旧悄悄地通着信息。
--不要哭,我的心。
我没有哭,我很欢喜,因为你又来了。
我只是在静静地等待,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答应过,你将转回来,带我同去。
拉赫趴在窗台上看了我好一会儿我都不觉得。
"做什么低低地垂着头?不睡了便起来吧!"她甜蜜的声音清脆地吹了过来,
我望着她微笑,伸着懒腰,窗外正是风和日丽的明媚如洗的五月早晨。
我们去火车站领出了行李便往飞机场开去。
"现在只是去画票,你是不快走的口罗!"歌妮不放心地说。
"等我手好了带你去骑摩托车。"安德列阿说。
"就为了坐车,等到你骨头结实起来呀!"我惊叹地笑起来。
"这次不许很快走。"达尼埃也不放心了。
在机场瑞航的柜台上,我支开了三个孩子去买明信片,画定了第二天直飞维也纳的班机。
那时我突然想起三岁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片中的母亲叫孩子去买大饼,孩子回来母亲已经跳江了。
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联想呢?
我收起机票对迎面走来的安德列阿他们笑。
"喂喂!我们去法国吧?"我喊。
"车顶上的大箱子怎么办?过关查起来就讨厌了。"安德列阿说。
"要查就送给海关好口罗!"我说。
"又来了!又要丢掉箱子了,那么高兴?"达尼埃笑了起来。
"放在瑞士海关这边嘛!回来时再拿。"我说。
"哪有这样的?"歌妮说。
"我去说,我说就行,你赌不赌?"我笑说。
"那么有把握?"
"不行就给他查嘛!我是要强迫他们寄放的。"
于是我们又挤上车,直往法国边界开去。
那天晚上,等我与维也纳堂哥通完电话才说次日要走了。
"那么匆忙?"拉赫一愣。
"早也是走,晚也是走,又不能真住一辈子。"我坐在地板上,仰起头来看看她。
"还是太快了,你一个人回去过得下来吗?"奥帝问。
"我喜欢在自己家里。"
"以后生活靠什么?"奥帝沉吟了一下。
"靠自己,靠写字。"我笑着说。
"去旅行社里工作好啦!收入一定比较稳当。"歌妮说。
"写字已经是不得已了,坐办公室更不是我的性情,情愿吃少一点,不要赚更多钱了!"我喊起来。
"为什么不来瑞士又不回台湾去?"达尼埃问着。
"世界上,我只认识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我海边的家,还要什么呢?我只想安静简单地过完我的下半辈子。"
火光照着每一张沉默的脸,我丢下拨火钳,拍拍裙子,笑问着这一家人:"谁跟我去莱茵河夜游?"
炉火虽美,可是我对于前途、将来,这些空泛的谈话实在没有兴趣,再说,谈又谈得出什么来呢,徒然累人累己。不如去听听莱茵河的呜咽倒是清爽些。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发觉又是新的旅程放在前面,心里无由地有些悲苦,就要看到十三年没有见面的二堂哥了,作曲教钢琴的哥哥,还有也是学音乐的曼嫂,还有只见过照片的小侄儿,去维也纳的事便这样的有了一些安慰。在自己哥哥的家里,不必早起,我要整整地大睡一星期,这么一想,可以长长地睡眠在梦中,便又有些欢喜起来。
虽然下午便要离开瑞士,还一样陪着拉赫去买菜,一样去银行,去邮局,好似一般平常生活的样子。做游客是很辛苦的事情,去了半日法国弄得快累死了。
跟拉赫提了菜篮回来,发觉一辆红色的法国"雪铁龙"厂出的不带水小铁皮平民车停在门口。
这种车子往往是我喜欢的典型的人坐在里面,例如《娃娃看天下》那本漫画书里玛法达的爸爸便有这样一辆同样的车。它是极有性格的,车上的人不是学生就是那种和气的好人。
"我想这是谁的车,当然应该是你的嘛!希伯尔!"
我笑着往一个留胡子的瘦家伙跑过去,我的好朋友希伯尔正与达尼埃坐在花园里呢!
"怎么样?好吗?"我与他重重地握握手。
"好!"他简短地说,又上去与拉赫握握手。
"两年没见了吧!谢谢你送给荷西的那把刀,还有我的老盆子,也没写信谢你!"我拉了椅子坐下来。
希伯尔的父母亲退休之后总有半年住在加那利群岛我们那个海边。跟希伯尔我们是淘垃圾认识的,家中那扇雕花的大木门就是他住在那儿度假时翻出来送我们的。
这个朋友以前在教小学,有一天他强迫小孩子在写数学,看看那些可怜的小家伙,只是闷着头在那教室里演算,一个个屈服得如同绵羊一般,这一惊痛,他改了行,做起旧货买卖来,再也没有回去教书。别人说他是逃兵,我倒觉得只要他没有危害社会,也是一份正当而自由的选择和兴趣。
"Echo,我在报上看见你的照片。"希伯尔说。
"什么时候?"我问。
"一个月以前,你在东南亚,我的邻近住着一个新加坡来的学生,他知道你,拿了你的剪报给我看,问我是不是。"
达尼埃抢着接下去说:"希伯尔就打电话来给拉赫,拉赫看了剪报又生气又心痛,对着你的照片说--回来!回来!不要再撑了。"
"其实也没撑--"说着我突然流泪了。
"嘿嘿!说起来还哭呢!你喜欢给人照片里那么挤?"达尼埃问。
我一甩头,跑进屋子里去。
过了一会儿,拉赫又在喊我:"Echo,出来啊!你在做什么?"
"在洗头,烫衣服,擦靴子呢!"我在地下室里应着。
"吃中饭啦!"
我包着湿湿的头发出来,希伯尔却要走了。
"谢谢你来看我。"我陪他往车子走去。
"Echo,要不要什么旧货,去我那儿挑一样年代久的带走?"
"不要,真的,我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好--祝你……"他微笑地扶着我的两肩。
"祝我健康,愉快。"我说。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希伯尔点点头,突然有些伤感。
"再见!"我与他握握手,他轻轻摸了一下我的脸,无限温柔地再看我一眼,然后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
就算是一个这样的朋友,别离还是怅然。
下午三点多钟,歌妮和奥帝已在机场等我们了。
我们坐在机场的咖啡室里。
"多吃一点,这块你吃!"拉赫把她动也没动的蛋糕推给我。
"等一下我进去了你们就走,不要去看台叫我好不好!"我匆匆咽着蛋糕。
"我们去看,不喊你。"
"看也不许看,免得我回头。"
"好好照顾自己,不好就马上回来,知道吗?"拉赫又理理我的头发。
"这个别针是祖母的,你带去口罗!"拉赫从衣领上拿下一个花别针来。
"留给歌妮,这种纪念性的东西。"
"你也是我们家的一分子,带去好了!"拉赫又说。
我细心地把这老别针放在皮包里,也不再说什么了。
"听见了!不好就回来!"奥帝又叮咛。
"不会有什么不好了,你们放心!"我笑着说。
"安德列阿,你的骨头快快结好,下次我来就去骑摩托车了。"我友爱地摸摸安德列阿的石膏手,他沉默着苦笑。"七月十三号加那利群岛等你。"我对达尼埃说。
"一起去潜水,我教你。"他说。
"对--"我慢慢地说。
扩音器突然响了,才播出班机号码我就弹了起来,心跳渐渐加快了。
"Echo,Echo--"歌妮拉住我,眼睛一红。
"怎么这样呢!来!陪我走到出境室。"我挽住歌妮走,又亲亲她的脸。
"奥帝!拉赫!谢谢你们!"我紧紧地抱着这一对夫妇不放。
安德列阿与达尼埃也上来拥别。
"很快就回来哦!下次来长住了!"拉赫说。
"好!一定的。"我笑着。
"再见!"
我站定了,再深深地将这些亲爱的脸孔在我心里印过一遍,然后我走进出境室,再也没有回头。
以后更新的频率是?
基本上,每一本书就是一天一章的量了。
小编
看得不够过瘾怎么办?
后台发送书名,找小编要电子书的资源就好啦!
小编
我想看的书,不是你更新的这些,可以更新一些别的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