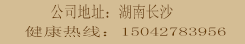一直就想写这个题目,我们这代人对“再教育”领会颇深,而将来对这段历史将要作出怎样的评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要把个人的感受写出来,起码是亲历者对她的真实评价。
所谓的“再教育”,我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段时间。就是某个人或某些人认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再一次接受教育。至于教育对象是谁,要视情况而定。那段时间的被教育对象是我们,(尽管我们只是小学毕业生,)教育对象是工、农、兵。
我是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生,因文化大革命的原因直到一九六八年才离开小学,大锅端到天津市第20中学,哼!沾了文化大革命的光,要是考试,还不定考得上考不上呢!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个20中学。到中学一看吓一跳。原来20中六个年级一共才有十二个班。我们河大附小、长沙路小学、西安道一小三个小学一下分进了十二个班。校园里挤得乌乌漾漾,老生都不拿正眼瞧我们。学校也没有那么多教室,得!正好,劳动去吧!中学两年多一点儿,有一多半时间是在学工、学农、学军中度过的。
先写学军吧!因学工、学农的时间太长,篇幅一定比学军长。
我们20中,学军的对口单位是天津警备区农场,在北郊区青光村以北。第一次行军走了三十多里地,脚上打泡的同学真不少。我们是步行的啊!正是暑热天,到了军营还没水洗,因为农场平时并没有多少兵。一下子来了二百来个学生,打他个措手不及。也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想洗,没门,先臭着。
下午,集合,由部队领导训话,内容不记得了,记得最清的是,给我们分排长,那时候学校都是部队编制,现在的班,那时候叫排。现在的小组那时候叫班。我们学校是男、女分班。给男生分的排长,用现在的话叫个顶个的帅哥,给女生分的排长全是歪瓜裂枣。我们有幸分了一个胖排长,我们班在学校就是个闹班,虽说是个女生班。但能量一点儿也不小。老师都有些发憷教我们班。看到胖排长,立即有人小声发话了:“胖子好,胖子跑不动。”第二天,出早操,各排都来到操场,练队列,站军姿,拔正步。我们排只在操场上站了一下,就被胖排长拉出来了,只听他喊了一声:“跑步走”一二、一二地就把我们拉到军营通大门的道儿上了,还没等我们闹明白怎么回事,就出了大门,上了乡村的公路,又跑了一会儿,就上了现在的京福公路,那时候京福公路没有什么车,两边的杨树高高的,因为是出早操,太阳还没出来,所以不太热。我们紧跟着胖排长也不知跑出了多远,反正后来只有十几个大个儿,多是小学业余体校的田径运动员跟上了他。队伍已经溃不成军,胖排长回头看了看,来了一个折返跑,把这十几个人带上,一路收容着我们的同学,可是脚步一点也没慢。跑回操场的时候,操场上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都去食堂吃饭了)只记得京福公路两侧高高的杨树在我们回来的时候洒下花花的树荫。
就这样,我们排连续跑了五天,我们都埋怨说这话的同学,她姓孙,我们给她起的外号叫“猴子”,我们说:“猴子,准是那天你说的话叫胖排长听见了,现在拿咱们出气。”猴子也懊悔不迭。其实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出力是长力的。第一天是溃不成军,后来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直到第五天跑回操场,胖排长在点评的时候才露出笑脸说:“嗯!不错。告诉你们,别看我胖,我就是能跑。”领教了。胖子真能跑。
学军的时候还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儿,就是,越下雨越在外面淋,越饿越得使劲唱,否则不能进食堂。最怕的是夜间紧急集合,排长那尖利的哨子声刚落,他的重拳就砸到宿舍薄薄的门板上了。“砰”“砰”“砰”“四排集合了!”平时说话声音不大的排长用声嘶力竭的嗓音喊出。吓得我们哆哆嗦嗦,尽管知道不定哪天晚上有紧急集合,真到时候还是害怕。发昏挡不住死,我们都用尽可能快的速度,穿戴好,跑出宿舍。“报告排长,一班到齐”“报告排长,二班到齐”“报告排长,三班到齐”三个班长纷纷报告。排长立即把我们带到操场。还好我们是女生排第一个到的。营长训话,大意是有一个美蒋特务刚刚跳伞,就在青光附近,我们的任务是在京福公路两边搜索,来个学生兵,在排长的带领下,在公路两边下沟上坎儿的干开了。没有手电,没有路灯,只有满天的星星照明。摔跤、掉鞋,屡屡发生。不敢说话、咳嗽。压低声音的:“跟上”,叫我们的脚步更加踉跄。也不知跑了多远,只见天色已微明,已能分辨出离你最近的人是谁了,排长从前头跑过来,后队变前队,我们又跑回了操场。现在想起来那的事儿呀!还美蒋特务?当时可是“真”的。
第二次紧急集合就更可笑了,在部队我们学会的第一件事是整理内务,第二件事就是打背包。把被子叠好,用行李绳三横两竖(横压竖)的捆结实,再弄双破胶鞋往后面一塞,背起来就能走。最主要的是不能散。打背包不是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这时候就看出来动手能力的高低来了。有人很快就学会了,有人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可第二次紧急集合偏偏要打背包。又是半夜哨响,又是“砰”“砰”“砰”的擂门声,只是又加了一句“把背包打起来,背上,快点”的说明。不许开灯,摸黑儿,可就乱套了,你刚把行李绳拿出来,转眼就不见了,她刚把背包带放上,不知又被谁抻走,谁也不敢大声说话,借着窗外营区的路灯,我们就这样慌乱的打起背包,跑出宿舍。这回没出营区,只在操场跑了几圈,天色就明了。营长训话,他没说什么,只是叫我们互相看看,再往跑道上看看,这一看不得了,我们都乐了。平时打得方方正正的背包,现在是七扭八歪,这还算好的。有人干脆打个大十字,背是不能背了,在胳膊底下夹着,操场跑道上好几只鞋。营长说:“就这样还想当兵,鞋都跑丢了,今天回去就练打背包,各排带回吧。”
军营一个月的锻炼,真的把我懒散的毛病改了不少。
回学校以后,坐在教室里,知足的不得了,我们开始上文化课,英语先学的是“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和26个字母。现在也仅存这些了。数学,学的是数轴,我统计过,连自学带后来上学,我一共学了五遍数轴。(基础比较扎实,哼)化学没沾边儿,物理只上了一节,好像是物质。对就是物质。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学给我的全部文化知识。
好景不长,我们刚开始学习,七0届又从小学顶上来了,他们比我们人更多,(马寅初先生您是多么的英明啊!)得,我们又开始新的一轮儿劳动,军是不用学了,留给新生吧!我们去刘安庄农场稻田队,打稻子。去王顶堤大队背稻子。去军粮城公社割稻子。哪个地方都有故事,只说军粮城的事情吧,因为到山西以后,我们时常回忆到它。
在军粮城我们呆了十天,除了割稻子,就是背稻子,因那是时机械化程度十分低,。全凭人力完成收割任务。我们去老乡也很欢迎。每天派一个大娘给我们做饭,十天,三十顿没换样儿,稻米饭,虾皮炒洋白菜或肉片炒洋白菜。我们跟大娘说:“煮点稀饭行吗?”大娘断然拒绝:“不行,你们每天干那么累得活儿,稀饭顶不住。”想想啊!小站稻啊!米饭蒸出来,上面一层油亮亮的,香着呢!我们却想着换口儿。后来遭了报了,到山西,稻米饭?棒子面也吃不饱。从军粮城回家后,我姥姥烙的发面饼,好几天了,都干了,我拿起就啃,香极了。闹了半天白面这么香。从那时就知道再好的东西也不能多吃,要有节制。
再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我们学工的单位是天津市手电筒厂,在小白楼音乐厅后面,离学校很近,但劳动是不用进校的。我们跟着师傅的时间表走,师傅上早班,我们上早班。师傅上夜班,我们上夜班。在我们前一期的学工的同学,在冲床上把大拇指冲掉了,所以工厂严令,学生不许上冲床。我的师傅姓什么已经不记得了,三十多岁,女的。话不多,不,不,不,不说话,叫我干什么都用手势,一抬手我就开机器,手往下一挥,我立即关床子。手往里一摆,我立即续料,手往外一摆,我马上停止续料。我们那台机器总爱出毛病,师傅拿把螺丝刀,这捅捅,那拧拧。敲敲上边,扒拉扒拉下边。车间里的活儿并不太多,因此我的同学经常串岗,看到我师傅这样指挥我都乐,回去跟她们的师傅学说,她们的师傅告诉她们,我师傅就那样,谁也不理。好了“老阿倔”的外号立即在我们中间传开了。时间长了,我们又给车间别的师傅起了很多的外号,只要外观上有特点,那绝跑不掉。什么“胡萝卜”“土豆”“番茄大博士”总之《洋葱头历险记》里的名字几乎全用上了。由于我师傅的严格训练,我眼神儿特别的好,也就是说有眼力见儿。后来到了山西,伺候匠人,(山西管有手艺的人称为匠人)比如给我们盘炉灶的人,我在旁边递砖、递灰,恰到好处。被他称为“不歪咯”。
在手电筒厂先后一共劳动过两个月,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初步认识就这样形成了。我的中学时代就这样度过了。现在不喜欢读书的孩子可能还很羡慕呢!这多“好”,一会儿去农村,一会儿去工厂,一会儿去兵营,就是不在教室里念书。我美好的中学时光很快结束了,这次可是真要当农民了。
在山西长子县当农民,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确实给我上了铭心刻骨的一课。农民自称是“受苦人”,一开始不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理解,农村那艰苦的生活,辛勤劳动一年所得甚少,我们知识青年就更是食不果腹,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后果不堪设想。食物的匮乏,造成我们整天就想着怎样才能填饱肚子。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也敢干。并不为耻。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认为,没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根本提不到。
贫下中农给予我的再教育,说老实话,真得不太好。他们心地善良,但极端自私,不赖他们,因为客观环境造就了他们这种观念。生存环境太恶劣了。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大变样了。但我们没赶上。
在农村,我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也不敢胡思乱想,每天下地劳动,盼着下雨,能休息一天。盼着邮递员带来家中和同学的消息。一年下来就盼着冬天的到来,能回家,吃饱饭。年的夏天,我们村的董津生选调到太原上学,我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点儿没犹豫,立即回家,正好是暑假,我想复习功课,来年考学。这种想法当然得到家庭的大力支持。
放暑假我母亲在家,整天就我一个学生,正好过瘾(我妈是老师,教书有瘾,或者是癖好)又是从数轴开始,因式分解、几何基础等等初中数学讲完了。高中数学刚开始学,在村里的同学就打电报来,叫我们回村说有选调任务。其他同学都回去了,我在犹豫,能有我吗?我这个人始终不自信,后来她们连来三封电报。我才下决心回村。72年11月1日我才到村里。回到庙里吓一大跳。情况和前几个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一进院儿,马津就大声说:“你回来了,怎么不打封电报我们上东田良接你去?”男生纷纷跑出来,都在问候。见到这种情况,我逃也似的奔向我的宿舍,问跟过来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插队两年多了,我们男女生同住一院儿,从不过话。老死不相往来。马津笑盈盈地说:“你适应适应吧,男生现在整天和我们说话,待会儿还叫咱们上他们屋里讲故事哪!”“你们答应他们啦?”“当然答应啦,你快洗洗,吃完饭咱们一起去。”真没想到,选调这件事把我们和男生之间的坚冰给打破了。
72年11月28日,我终于选调到长子柴油机厂当了一名学徒工,我们进厂共20名知青。五个男生,十五名女生,为什么男女比例如此严重失调,后来我们才知道,招工的人根本没翻档案,只是凭名字就判断是男生和女生了。像我这样的名字当然被当成男生招进厂了。简直是混水摸鱼。当时我还深怕给退回村。
终于当上了工人,不用在和太阳亲密接触,不用管那摸不准脾气的炉火,不用挑着扁担上山下沟,不用再干锄也锄不完的地。收也收不完的秋。每月17元的生活费除了买饭票还略有盈余。长子新华书店我是跑熟腿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两地书》《呐喊》《彷徨》都是那时买的,才两三毛钱一本。
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就必须说一说我的师傅李文章,李师傅是河南林县人,当年不到四十岁,瘦瘦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后来我问过李师傅眼睛的事,他说是小时候饿瞎的。我们刚进厂,好像名声不大好,(不知什么原因)别的人都不爱带天津知青,李师傅就一个人接下了我们十几个徒弟,当时我们分在金工车间,机体组,一条流水线,从毛坯进车间走完我们这条线,就进装配车间了。我们都是生手,李师傅就挨个儿教,从来没发过火。我们中间有心灵手巧的,例如张大泽、吉秉钧,他们都很快就独立操作了。这样的人我们给起外号叫“大徒弟”。当年我也是很努力学习的一个。但是“大徒弟”没当上。李师傅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在思想上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为人正直,对徒弟一视同仁,刚进车间的时候,李师傅总是一路小跑从流水线这头跑到那头。八小时根本停不下来,后来我们都能自己操作了,李师傅就能坐下来跟我们聊几句天。记得清楚的事是,师傅拿一支石笔,在破桌子上,寥寥几笔就画出了活灵活现的小鱼和展翅高飞的鸽子。我对绘画是一窍不通,但师傅画的小鱼和鸽子笔划实在不多,我在旁边临摹了一会儿就有几分像了。后来就用这蒙小孩儿。(包括自己的孩子)
我们进厂时间不长。厂里就转产干手扶拖拉机用的柴油机,型号是。我们这条流水线整体报废,换另一条专用流水线,对于学技术靠手艺吃饭的人来讲,这真是好时机,通过这次换线,我们接触到原来根本接触不到的工艺流程,李师傅带着几个“大徒弟”没明没夜的干,我们几个女生每天只是帮助拉拉大绳,也就是帮助把旧设备拉出车间,把新设备拉进车间。如果没有这些活儿,就去车间别的工段帮助人家加点儿冷却液之类的。
在工厂
有一天李师傅叫我上车间办公室上面的小楼,我进去一看,只见七个木板一字排开,几个男生坐在旁边,另一边还放了一堆电器元件。李师傅告诉我们,车间的新设备都是我们自己厂干的,设备上的配电盘由我们几个人来做。由于设备大同小异,为了赶时间,决定一起做。现在你们每个人站到一块木板旁边,听大泽讲怎样安装。第一次听说我们中间居然有懂电的。当刮目相看。就是大李村的张大泽。他站在黑板前,详细的把电器元件的安装位置讲清楚。这好办,我们都有一双灵活而有力的手,很快就安装完毕。到接线时,我才知道无论多复杂的配电箱只用三种颜色的电线,它们是主线、控制线和灯线。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装配电板。张大泽在黑板上详细地告诉我们,用什么颜色的电线,从一个接触器上的某一个点接到另一个接触器上的某一点。什么长开点,什么长闭点的,我就照猫画虎的接吧!干了一会儿,我就发现问题了,我旁边的这个家伙。他接的配电盘好看,各色电线都错落有致的排着,横平竖直。我这却七扭八歪的,我立即举手示意,大徒弟先等等,我有问题。张大泽停下来,我问我旁边的家伙:“你接得怎么好看,我的这个配电盘怎么这么难瞧。”这位老兄不紧不慢的说:“我做每根线的接头都是一钳子口,高低也是一个尺寸。”地雷的秘密探来了,我对张大泽说:“你等等吧!我得整理整理。”其他的几位马上响应。李师傅站在旁边只是微笑,不点评、不帮助。可看得出来他真高兴。
进厂一晃就快三年了,我的上学梦还没醒,又听说厂里有上学的名额,我开始蠢蠢欲动,下了班找出数学和语文书,开始又一轮的学习,还是数轴。我和师傅说,李师傅说那恐怕要厂里推荐,我就去找当时的革委会,办公室主任刚开始敷衍,后来我又去找,他直言不讳的说:“你不行,你那档案里太乱。”一句话把我从办公室里撅出来。好在我这个人天生没心没肺,当时别扭了一阵儿,过后又安心的当我的工人老大哥了。
出师不久,有机会我调回了天津。上中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曾经问过我:“你是愿意到一个大单位去当一名小员工呢?还是愿意到一个小单位去当头呢?”本人一贯头脑简单,根本没想过,我就反问她,:“那你呢?”她回答:“我想到大单位当小员工,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当时她家也受到冲击了。我想想,也是啊!这次如愿以偿,我调到一个新建的中型企业,去当我的老大,(当时工人俗称老大哥)该知足了。
我始终认为工人作为阶级,是伟大的,对工作精益求精,对事业无私奉献。这不,在摸着石头过河时期,第一个牺牲的还是工人阶级。或者说第一个献身的是工人阶级。
谁承想,年科学的春天来了,老九翻身了(当时知识分子俗称老九),也不知是谁,想起了什么,提出从六八届至文革期间的所有初中毕业生全部回炉,补习初中文化课,当时这些人可都是生产骨干,从一线上全部撤下来学习,生产任务不能保证,车间主任就不干。我们厂的教育科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分批参加学习,每学期顶多六十人,车间也顶不住,因为当时涨工资的条件之一就是初中补习及格。
我是第三批的学员,先说说我们的老师吧!说出来的羡慕死你们!我们厂是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老师根本不用外聘。教数学的刘老师是特设科的,北航毕业。教语文的刘老师是技术科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来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镀金,再后来是我们厂最后一任总工,教几何的韩老师,西北工业大学毕业。教化学的赵老师,中心实验室的,天津师范大学毕业。教物理的刘老师也是西工大的。现在的高级中学教师配备也不过如此吧!那时却教我们。
这就是我第四次学数轴,基础可谓扎实吧!教数学的刘老师,平时不苟言笑,我对他是敬而远之。可是上课以后,发现这位老师太好了,科代表敛上作业,交给他,他总要问一句“齐了吗?”如答“不齐”,就要追问“为什么?”所以科代表,一回教室就跟没交作业的同学说,再不交作业自己去跟刘老师说。我们班的数学作业交的是最齐的。我见过刘老师的教案,是我生平见得最好的教案。我也算见识过的人,因为我母亲、姥姥都是老师,我从小又是在耀华中学高中数学组长起来的,本人也曾混进教师队伍三年。但是刘老师的教案真是首屈一指。那么整齐、那么详细,教案上的图比我们在坐标纸上画的都规矩。
再说教化学的赵老师,师范毕业,教学有一套。现在想起来都想乐,每天下午课是最难熬的,困呢!赵老师不怕,见学生趴下的多了,就叫起一个平时识逗的,也就是脸皮厚的,能配合她演戏的,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赵林建,当时他已经三十出头了,还没结婚,厂里正分房,他人坐在教室,心在分房小组。下午上课他必定要小息一会儿,赵老师就把他叫起来,提问题叫他回答,他就开始胡说八道,经常是他一起立我们就开始醒盹,他一张嘴,就是哄堂大笑,赵老师有这个能力,忍住不笑,继续提问,继续胡说。笑声连打鼾的人都能震醒。此时只见赵老师一摆手,叫他坐下,扭头问我们“还困吗?”“不困了”“好,那听我讲课。”这就是师范出来的。
教语文的刘老师本身是学工的,哈军工的高材生,教语文,我心里打个问号。可一上课就知道了,什么是文理并茂。课讲得确实不错。记得第一篇作文,就是写一封信。我正好有满腹的牢骚要发,你还给我机会,我一点也没犹豫,把要说的话和盘托出,什么该上学的时候不让学,现在孩子小,家庭负担重,工作一摊事,人在教室座,心思在外边等等。这可是你叫我写的,不是我自己要写的。没想到点评作文的时候,刘老师居然拿出来了我的作文,当作范文来点评。我摆出来一幅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心想,你随便说,我说的都是实话。他从我的作文中摘出一段话,告诉同学,这是排比句。写文章经常要用。
我的再教育就此打上句号,后来我调入科室,没有文凭不行,我就参加了成人教育,在天津机电学院浑了一张大专文凭。回想我这辈子不管是教育还是再教育,都不是主动的。好容易退休了,又上了小屋学苑这条船。还是用广告语结束这篇文章吧,教育终生,终生教育。
本文作者岳东升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tealabo.com/sbyl/52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