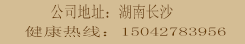/12/3周一
实习第一天。上午在写采访提纲,下午出去采访。
一位老人家住在养老院。我和居委大姐骑着小黄车过去,路上了解情况,得知老人家80多岁,前几年住进养老院,生活不能自理,记忆也不太清楚。有些担心采访能不能进行。
第一次进养老院。小时候进过村里的老人组,见到的都是身子骨硬朗的老人家。这次进养老院,看到的都是靠轮椅和拐杖行走的老人家,我们去时,她们乘着轮椅排在走廊两边,各自休息或私语,或者盯着白墙和电视发呆。
不出意外,老人家什么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年轻时在砖厂做工,做了一辈子,其他都不记得了,奖项、个人经历、入党经过,全都记不得。
居委大姐帮忙问了几个问题,老人家都不记得了,只是一直在说你们过来看我我很高兴。
后来她儿子来了,60多岁了,看起来身体还行,跟我们聊了几句。后面不知为何,忽然跟我们说他真的不是不孝,但凡老人家能多走一步路,他都不会让她来养老院,但是前几年老人家生活彻底不能自理,他跟母亲男女有别,有些事不能照顾,妻子也是60多岁身体不便,最后没办法才送来养老院,但也是送最好的养老院,而且每天都过来看她,‘“我也是迫不得已。”
”我也不清楚她的事,几十年前的了,怎么记得住?”他说。居委大姐跟我说我们回居委,这样采访不了的,我找她的档案给你,你再看看能怎么写。我说好。后来回到居委,大姐找了很久找不到档案。
/12/4周二万人工体
今天三个采访。
上午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家,身体不错。因为上午只安排了一位采访对象,所以没有刻意去控制时间,敞开了聊,聊了一个小时吧。
60年代,他考到北京上大学。家境清贫,但学校对学生待遇很好,每月十几块钱补习费都由学校出,此外每月还发两块钱零用钱。他在学还有一段故宫的兼职经历,上学之余,在故宫里扫地。
年毕业,他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几万个大学生在这里。周在台上开报告会,报告标题是《革命与劳动》。周讲:“毕业以后要跟工农相结合,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积极参加劳动、参加革命,不断学习,坚持做下去。”他把入场券保留到今天,周的话也记了几十年,之后的一生便是听组织安排,作为工程师四地奔波的一生,年老时,归根调回广州。说,“这里有亲人。”
到最后我合上采访本子时,老人家也放松了,还主动说起他孙女,在海外留学,打开钱包拿出照片给我看。
下午一位采访对象是个很凌厉的老人家,直接抓走我的本子,说她要先看一下问哪些问题,她做个准备。
看过问题后,老人自己情绪饱满地演讲了30分钟,我插不上话,只能尽力把控方向,再偶尔插问细节。
但也会触及到一些破碎的地方,偶然提及到计划生育,她是当年村里抓计划生育的队长,抓到了偷生的,则要扭去打胎。她还记得当初打到一个孕妇,八个月,胎儿掏出来是个成型的男婴。
“居然是个男婴。”她说,“这是叫别人断子绝孙的事啊。”
“真的不是我想做的啊,但这是任务安排。”她说。
“聪明点的,连夜跑了,到山里去,到其他抓得比较松的地方去,不跑的都是太老实了。”她说。
“我也不想做啊。”她说。
“我们村计划生育是做得最好的。”她说。
“那些年我常常做噩梦。”她停下来。居委的人上去安慰她。
/12/11周二孤儿
前往一户采访对象,老人家卧床,起不来。躺在床上八九年了,说是工作时太累把身体做坏了。年轻时,她是纺织厂班长,因为表现优秀被推荐入了D。劳动最光荣的年代,D员多揽活。她啐了一口说,站的越高,别人越盯着你呢,巴不得你出事。
劳累半生,但退休不久便瘫痪了。瘫痪原因不知,家人只说是早年加班累的。在床上很多年动弹不得,老伴又在前两年去世。她不愿意接受采访,戾气比较重,说这么多年GD也没派人看过她,现在只会搞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又说自己卧床废人一个,没什么好采访的。
全程有点难受,勉强把要问的问题都问完了。可能因为态度比较好,后面老人家儿子也愿意帮忙说几句,还帮我找老人家的照片找了很久,虽然最后没找到。
另一位采访对象是一位78岁的大姐,看起来和蔼漂亮。我刚问第一句话,她眼泪便滑下来,随之哭了起来……我们只好安慰她,说不好的回忆可以不用想。她还是边哭边讲。
她是孤儿,父母在饥荒中死去。她被养母抱走,童年在乞讨中度过。建国后,她被允许上学,考上护士学校,迎来了转机。此后又入了D成了战地护士,搬运尸体,同事不敢,她率先上去,“也害怕,但看惯了。”和平时代她成为值班最多的护士,同事有事缺勤,她都主动顶上,她觉得是做好事。医院晃悠,看到需要帮忙的就过去。但个人睡眠时间变得很少,自己偷偷吃安眠药,后来胃出了问题,被医生制止。
前半生是苦的,但后半生是甜的。丈夫是科学家,在护士学校看上她。两人恩爱,有了两个孩子。后来丈夫调任到石家庄,她带着两个孩子,坐着火车奔去找他。此后几十年无论调任到哪里,两人都一直在一起。
/1/9癌症
苏伯是普宁人,跟他用潮汕话聊起来,但聊不顺口,最后还是换成了普通话。
他带了一个小包,聊天时打开,里面都是各种勋章奖章,金灿灿,漂漂亮亮。他一个个拿出来摆在桌面上,这是哪一年得的,那又是哪一年得的,他记得很清楚。他问我喜欢吗?“送给你”。我说你留着吧。
聊完出来,他跟我们说他得了癌症,15年检出来的,后来做化疗、吃药。前阵子还住了8天医院。居委说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他说现在是保持乐观,能活着就好了。走的时候他好像想跟我一起坐车走,但是居委催我赶紧去下一家采访,所以只能跟他说再见,留他一人慢慢回去。
下一家是上门采访。我们走进一个老旧的小区,环境不是很好,光线昏暗,墙上有污垢和裂痕,旁边也有人在施工,一直突突突地响。
敲门后,帮我们开门的是另外一个人,戴着帽子,衣服素朴,头发有些花白,没有话语。我没看清他的脸。李伯伯驻着拐杖站在门后,特地起身过来迎我们了,他前些日子刚中风做完手术,腿脚不便。
采访开始之前,跟李伯伯说要录音,他说可以。阿姨忽然冲过来了。我不知道她从哪里过来的,刚才一直没注意到。她直接说我不同意。跟我们说他刚做完手术,脑袋不是很清醒,可能会说错话,她不同意录音。接着跟我们讲起伯伯的事,说,他在工作上先进,是好人,在家里就不是了,他爱工作,爱党,但是不爱家,不爱老婆不爱孩子。说着就哭起来了。
我们让阿姨坐下来,她在旁边控诉。我拿了纸巾给她,阿姨没管我,讲了很多,讲完便自顾自离开了。可能回到了房间里。
后来了解到伯伯分到的房子不是很好,比较破败(刚才已经看过),有两个小孩,其中一位有精神障碍,就是前面给我们开门的那一位,跟伯伯阿姨住在一起,也是很大岁数了。伯伯不愿多讲,我们也没有问。感觉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
聊天过程中,发现他只是一心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他是搞技术的),没有追求政治或其他虚名。他是华工毕业的,讨论起技术上取得的成果和带过的学徒,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前面的苏伯偶然提起他,说他是个很老实的人。
但在阿姨的控诉里,大概知道他是只想着搞技术,无条件听单位安排,很少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什么,故而有很多委屈,都是一家人陪他受着。
/1/18Lifesucks发工资了,工资好低。两点钟醒来时手贱点了Novo的《FromGold》听,而后就陷入疯狂的愁绪里,这是我最听不得的歌,每次听到它我都会想起CYS。他在中国青年报。我前几天看到青年报的校招,但是我没投。我挺想跟他当同事的,但是我应该连简历关都过不了吧。刷朋友圈看到高中同学在中国经济周刊实习,出席一次大型商业活动,采访董明珠。感觉我的人生糟透了。/1/21宿舍时间周末两天一晃而过。周六跟室友大扫除,把宿舍清理得干干净净,开心。我的HUGSY也在阳台晒了一下午太阳。这两天阳光都很好。周日跟室友出去聚餐,每人一个大猪蹄子。才发现我们宿舍八个人,八个不同的职业。一个HR,一个教师,一个警察,一个银行柜员,一个行政助理,一个考研的公务员,一个出国,还有我。脑袋一直昏沉沉的。昨晚没睡好,梦见自己上班迟到了,一路赶车,特别疲惫,仿佛真实开始了一天。而后醒来,看了下手机6点22,睡去,而后醒来时再体验了一次梦里的情况,一路赶车。感觉一早上重复赶了两次公车和地铁。/1/24新年将至昨晚下班忘带钥匙,室友也不在宿舍。室友走前帮我把外卖放在宿舍里了,但是我进不去。在隔壁宿舍玩了一会猫,又出来走廊吹风,好冷。可惜身上没带烟。等了一个钟,室友才匆匆赶回来。万幸饭还是温的。早晨起来,正洗漱着,室友拉我到阳台,说你看。是一轮圆润红日,从教堂旁边升起来,天边一层薄云,边缘染出一条红色光带。漂亮极了。在公车上昏昏欲睡。这些天在听古典乐,好希望自己也会弹钢琴啊。昨天买了GS杂志,25块,好贵好贵,一直免费看GS的文章,25块还好了。就是最近穷到不行,花呗欠了2K,工资也还没发(也没有多少),是个很穷的新年了。我好困好困,想要沉沉地睡去。/1/25上午到离职干部休养所。休养所里面好大好宽敞,居委说有几百户人家吧。生活很休闲了,很多房子还带一个大院子。采访的老人家很好聊天,耳朵有点背,但是感觉很敏锐,她大儿子(也是六十多岁了)在旁边帮忙讲很多。儿子讲的时候老人家就安静下来,但神奇的是每次我一把目光移向老人家,她便回过神来心领神会地开口。我拿到了她的一个红本子,其中一页记录着她家人的出生时间和参加工作的时间。第一行是丈夫的死亡时间:清年5月9医院去世,农历四月初三。老人家没有很难过,她已经四代同堂了。采访结束后我们在她家门口拍了照。她家门口可以晒太阳,老人家坐在轮椅上。/3/7周四朋友发我一个凤凰新媒体的招聘,找做深度人物报道的记者。我对自己的能力和学历都没有自信,我很想做深度报道,但是觉得自己目前的学识撑不起我做这个东西。目前还是很迷茫,但是我知道有个方向有个目标在那里,但如何走过去,哪里有路可以走过去呢?/3/8我这些时间在听齐豫的歌,听李泰祥,听三毛的电话录音。对那个环境充满了向往。第一次看三毛是初中,大头买了一本三毛全集。我那时候经常去大头那里玩,拿着她的书一看就是一下午,我记得她有三毛的书,还有琦君的,其他便不记得了。那时候把三毛借回家,一整个暑假都在疯狂地看,看到她在沙漠里见到UFO,就觉得哇怎么回事,跑去问大头,这是真实的故事还是虚构的?她也说不出来。很多年以后我释然了,真的也好,假的也好,她能给我带来奇妙的感受就好,文学里也不分真实和虚构的。前段时间写了《骆驼》,朋友看完问我里面的故事是真的假的,说感觉像是真的又像是假的。我说这个不重要吧。我记得《批评的解剖》里有一段很毒舌的话来着,大意是说还执着于分辨故事真假的读者不配读文学,我看到这里真的拍腿大笑。说到分辨真假,因为近些年非虚构写作流行起来了。非虚构写作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种强大不是来自于这种写作模式,而是来自于生活。这几个月采访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世间的苦难是不间断的,天地不仁,众生纷纭。眼前这个人坐在你面前,带着过去苦难的印记,穿过了几十年,此刻坐在这里了,这种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文字的力量很微弱,感觉真正的不幸是令人哑言的。一切苦难都没有声音。所以非虚构写作的话,是在担任传声筒,是一个导体,是个WIFI放大器,把生活的声音放大出来给人听,哪怕我们听到的是无声的呜咽,它把生活的力量传过来了,我们感到震撼,就像一个大法师(生活),用它的法杖(非虚构类作者)向你发射了一个火球(非虚构作品),一下把你炸了。这种时候真实性是最重要的,它把生活的一个真实的层面释放出来。它到底和小说散文一类不同。之前拿了作品给系里的老师看,她说希望你写非虚构。但是我现在依旧会只想写虚构。我会去接触真实的东西,所以我来做采访,但是最终我想要的不是去呈现别人的生活,我去接触外界的事,不过是把他们拿回来,作为一块积木,最终和其他积木一起拼成我想要的模样,这是我写“虚构”故事的原因。众生悲怆,但我最终是向内的,我相信众生都会死亡,一切都会隐于无声,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么便没有谁更值得,那便只关心自己了。这个层面上,我成为不了一根优秀强大的老魔杖,但我是一个蹩脚的菜鸟法师。/3/11这一天请假,在学校跟导师讨论论文。早晨便开始做噩梦,梦见室友说导师给我们写好论文评语,发在论文系统里。我在梦里点开看,收到导师的评语是“装神弄鬼用了一堆术语,结果写出来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心情超难过。在梦里抓住室友问他我是不是在做梦?说好希望这个只是一个梦,然后在梦里到处跑来跑去问别人我是不是在梦里……上午醒来发现出太阳了,此前广州已经下了一周的雨,整个学校看起来都有些浮肿。上班的室友发了信息让我帮他晾衣服。我晾了衣服在阳台坐下来,一边晒太阳一边翻萧红的呼兰河传。在阳台上又兴起写了一段文字,是自己未来一篇文章的结尾,觉得漂亮极了,打算发朋友圈,编辑一半又删掉了,后来发给别人,被说像百年孤独,我假模假样地说真的耶。同时刷朋友圈看到隔壁寝室失踪半个月的猫找回来了,瘦了一大圈。晚上跟室友去看绿皮书。看前半段还是会有一种距离感,感觉文化隔阂,身在国内不会太懂黑人在美国的处境。不过中间黑人小哥的gay身份一出来,我马上就理解了,一点即通,他所有行为和心理我皆懂得了,真是一件奇妙的事。站在政治正确的角度,我会给它打高分并希望更多人看到它。新京报书评周刊也提到它,说“绿皮书”式的政治正确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现在“政治正确”仿佛成了一个反讽的词,很多人觉得反感,很多笑话拿它作梗,后者我会觉得不道德,仿佛一个平地上的人在作弄一个挂在悬崖边上的人。很多人只是浮在河面上,不知冰下的人如何生存,不知他们要遭受怎样的困境。在这层意义上,继续推广“政治正确”的作品是一场人类与人类的交流,是不同族群间的对话,“Youneedtofeelmypain”,大概仅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往文明的高处走。另,我最近在重温《寻》,早先几年没看懂里面的情感纠葛,只是觉得一个漂漂亮亮的世界里一群漂漂亮亮的人走来走去很有意思,它是我推开gay世界大门的一部启蒙作品,后来出的电影版结局,我翻来覆去看了两三遍,每一遍看都觉得有新的感受,大抵是自己的情感也正在生长着。到了《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懂得一些得到和失去,看到它时,心里是感同身受的,Elio父亲的那番话,也是在抚慰着我。所以觉得,现在再去看《寻》,我会看到更多的东西。“Ourheartsandourbodiesaregiventousonlyonce,andbeforeyouknowit,yourheart’swornout,and,asforyourbody,there转载请注明:http://www.shatealabo.com/sbzz/5080.html